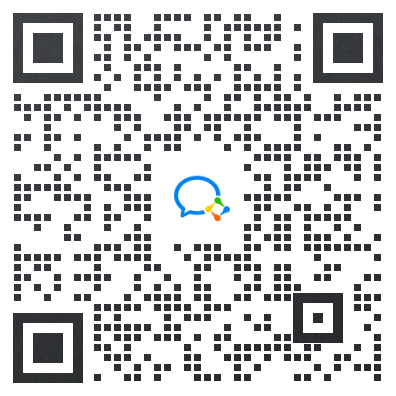写在前面
大约13年前,北大的BBS上一群热血青年对于“量子力学”展开了激烈讨论,有那么几位物理学爱好者分别认领了自己的科学偶像,以人物传记的形式,用不同的角度记录了量子力学的发展。小编恰好认识作者中的一位,这篇是以“波尔”为人物主线进行记录的,感谢原作者“时间的孩子”的分享,也希望借助此文的传播能使得当年那群热血青年重聚。
生活这场伟大的戏剧中,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这是一个古老的真理。
——N.玻尔

尼尔斯·亨利克·戴维·玻尔
(丹麦文:Niels Henrik David Bohr,1885年10月7日—1962年11月18日),丹麦物理学家,哥本哈根大学硕士/博士,丹麦皇家科学院院士,曾获丹麦皇家科学文学院金质奖章,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2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秋天的哥本哈根是多雾的,即使你起来很晚,也只能看到太阳迷离的面孔。白色的教堂,尖尖的钟塔亦是若隐若现,一切仿佛都是浮在梦中的国度里。于是你就大致可以明白为什么举世闻名的安徒生和他美妙的童话故事会诞生在这个同样美妙的北欧小国里。
即使是老练的当地人也经常会在雾中迷路,明明种在门口的梧桐树转眼即逝,而狭窄的小巷和宽阔的广场会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出现。当你终于费劲心机摸到一座 灰黄的四层楼建筑跟前,抬手拭去额头的汗水,一定会想要在这样的重重迷雾中寻找一条道路是多么不易呀!
你可曾想到,当年在这座建筑物里工作的一批年轻的物理学家们,又是怎样在如此的无尽迷雾中找到出路,并从这里延伸出去改变了整个二十世纪的命运?
这栋建筑物门前的牌子上面的字迹有些模糊,但仍可辨认出是这样几个字:"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学研究所"而底下的署名"尼尔斯.玻尔"虽经岁月的无情洗礼仍旧金光闪闪。
如果有机会随意采访一个物理系毕业的年青人,问他若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他会选择历史上哪个时期来从事物理工作。他们会不约而同地告诉你是本世纪二十年代。
那是任何一个有激情的年青人都可以仗剑走江湖的年代。经典物理学象多骨诺米牌一样哗哗倒地。头发花白的老学者们徒劳无望地支撑着牛顿力学的大厦,而年青人们旋风一般的思想让他们既兴奋又恐惧。
不管你是刚走出校门的毕业生,还是刚对物理发生兴趣的门外汉,都有机会崭露头角。一篇简短而深刻的论文就会使你永铭物理学史。权威们在新锐面前退缩,冲锋的号角在耳边一遍又一遍响起,他们身上的血液随时都在沸腾。那个时代是十足属于年青人的。
1
1895 年,德国的伦琴发现了 X 射线。
1896 年,法国的贝克勒尔发现了放射性。
1897 年,英国的汤姆逊发现了电子。
临近世纪末,上帝突然变得躁动不安,他扔下一大把谜语,然后默默不言。陶醉在牛顿经典力学无往不胜的压倒性战绩的人们隐隐觉得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自然界还是有很多神秘现象没有解释。
且不说伦琴目瞪口呆的望着 X 光照出来的他夫人的手指骨,也不说贝克勒尔莫名其妙地看着被感光的底片,就说汤姆逊亦是眉头紧锁,对他发现的这种奇异的带负电的小粒子一筹莫展。
汤姆逊是一位物理学界的老前辈,他虽出身贫寒,但凭聪颖好学很快就显示出他在学界的实力,年纪轻轻就成为卡文迪许实验室的主任,然后是皇家学会会长,剑桥三一学院的院长,成为牛顿的继任者之一。
可是本当兴奋的他却极不情愿地向学界宣布他的新发现。
可以理解他的窘状,当时的世界尽管铁轨遍野,电线密布,工厂里的机床彻夜地运转,但是人们对微观世界的认识还停留在遥远的古希腊德谟克里特时代。大家只知道原子是世界的本原,但谁也没想过原子到底能不能再分。而可怜的汤姆逊居然把这种比原子小得多的东西找了出来。
这个叫电子的小东西虽然看不见,但是你可以精确地感知它的存在,你可以测得它的质量,电荷,速度,甚至在它运动的路途上加上磁铁,你会觉察到它的偏转。
真是个幽灵。
然而学界一阵喧闹之后,就沉寂了下去。汤姆逊本人进行一段时间后,也悄悄终止了研究,毕竟还有其它太多的事情要做。
这些小玩意儿,留给后来人吧,汤姆逊呷完最后一口咖啡,合上了实验记录本。
甚至在十年之后的 1907 年,这片阵地还几乎还是一片静寂。
在那一年里,名躁一时的爱因斯坦发表了光量子假说开了第一炮后又匆匆转移到广义相对论中去。
—36岁的新西兰人卢瑟福答应在英国领导著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
—22岁的哥本哈根大学学生尼尔斯.玻尔正在足球场上一边心不在焉地守着球门,一边用粉笔在门框上排演着公式
—20岁的薛定谔在维也纳大学里认真地记着笔记
—6岁的海森堡还在慕尼黑街头不知疲倦地和伙伴们玩着石子
老师的工作注定要由学生来完成。
体魄雄壮的卢瑟福刚来到英国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时候,他的洪亮的嗓音吓了所有的同事一跳。他一看就知道是那种体力充沛的人,但晒得红红的皮肤,粗糙有的大手使人更觉得他适合在菜园里栽种马铃薯。好促狭的英国人不客气地称这位外乡人是南半球的野兔,因为擅打地洞才来到了英国。卢瑟福听说了也没发火,他竭力显示自己绅士般的好脾气来和自己粗豪的外表相对照。他相信凭借自己的能力一定会在这里取得一席之地的。不久,他的导师汤姆逊让他研究电磁波,他在几个月内就把仪器的接收范围改造到半英里以外,充分显示了他在实验上的天才,从此汤姆逊对他青眼有加,甚至在自己退休之后推荐他继承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的宝座。
在1909年,卢瑟福拣起了老师锁在抽屉里的手稿,他开始认真考虑原子的结构问题了。
在几年前短暂而热烈的讨论中,学者们纷纷提出自己对原子结构的看法而其中以汤姆逊的建议最为出名。他幽默地称电子就象面包里的葡萄干,而带正电的物质象面包一样均匀地分布于整个空间。但是有人更带有哲学意味地提出行星模型,带正电的物质在中心,而电子在周围飞速的旋转,他们认为宏观的宇宙和微观的原子的组成应有暗合之处。
鉴于发现者汤姆逊的威名,学界勉强接受了他的解释,可是明显几种解释都有漏洞,在汤姆逊的面包中,带负电的葡萄干似乎在电磁引力的作用下很难静止不动,而行星模型中飞速旋转的电子按迈克斯韦的理论没有理由不向外辐射能量,最终也象陨石一样坠落到中心去的。
在此之前,卢瑟福已经从铀的辐射中分离出两种射线,一种是贝塔射线,也就是老师发现的电子,一种是阿尔法射线,这种射线比最轻的氢原子重四倍,带的电则是正电,而且电量是电子电荷的两倍。
这种更重的射线有个神奇的性质,就象传说中的点石为金一般,它可以将一种元素转为另一种元素。实验成功的消息刚传出去,立刻导致了欧洲黄金市场上的价狂贬。报纸上带有问号的巨大标题是,原子已经分裂,人类末日是否来到?而一些投机商的眼睛
放出了光芒,在他们眼里卢瑟福那群人是二十世纪的炼金士,于是实验室里经常接到豪门巨富的大额捐款。
金钱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不是坏事,卢瑟福添购了更新的仪器,卖力十倍地干起来。他卢瑟福办事的精力和效率是有目共睹的,但糟糕的是他喜欢以自己的体力为标准来要求其他人,经常导致实验室的人陪他一起饿肚子。慢慢他的外号不再是"新西兰的野兔",人们敬畏地称他为"鳄鱼",也许他对未知世界的渴求只有饥饿的鳄鱼对食物的贪婪才能一比。没想到卢瑟福对这个外号很满意,后来居然经常以鳄鱼自居。直到今天,在卢瑟福的纪念馆门前还伏着一只张牙舞爪的鳄鱼雕像。
不料,鳄鱼很快陷入了困境。在实验中绝大多数阿尔法离子自由自在的穿过了靶原子,但是有的偏离的原来的路线,甚至倒转回来。这就匪夷所思了,按照老师汤姆逊的模型,带正电的面包不会轻易让阿尔法粒子随意穿过的,而沉重的阿尔法粒子更不会被轻飘飘的电子反弹回来,其情形如同一颗疾驶的炮弹被蚊子一挡反弹回来一样可笑。
当时的实验条件用现在的眼光看当然简陋无比,一切都只能靠肉眼观测,蓝幽幽的硫化锌屏幕上每出现一个亮点就表示有一个阿尔法粒子反弹了回来,可是一万个粒子中只能有一个碰上这样的运气。卢瑟福所能作的只是平心静气地面对屏幕,一个亮点也不能数错。不幸的卢瑟福虽号称鳄鱼,但是却不具备鳄鱼捕食时超常的耐心。其实不光是他,任何人盯着屏幕超过五分钟都会因为两眼昏涩,金星乱舞产生误记数从而悻悻地退出观测的。他把乏味的枯燥工作交给了别人轮流,自己埋头红着眼睛叼着雪茄陷入深思,究竟什么原因有为数不多的阿尔法粒子竟被打得倒转回来?
仿佛一个人在扔硬币,连扔一万次都是正面。在概率上的极度荒谬一定意味着深刻的物理内涵。那意味着什么,难道原子内当真有一个质量集中的小核,射过去的 粒子只有擦近核的时候才会发生偏转,如果正好撞到核的时候就会反弹回来,而回来的粒子几率极小的原因是小核占整个原子的体积太小了,如同足球场上的一粒石子。
原来如此!
卢瑟福狠狠掷下未抽完的雪茄,很快即使一楼负责看门的耳背的老头儿也听到一声大吼,"我知道原子是什么样子了!"
"量子"这个词语是在 1900 年 12 月 14 日,在德国物理学会举办的一次会议上,从一个叫普朗克的大学教授嘴里第一次说出来的。在上帝的安排下,它和二十世纪是一起诞生的。很难用几句话概括这个词语对二十世纪的深远影响。如果大家还对利用对冲基金的杠杆效应掀起全球金融风暴的祸首索罗斯有了解的话,应该知道这位金融巨鳄的基金会的名字叫"量子基金会"。对这个奇怪的名字索罗斯的解释是,量子最大的特征就是不确定性,就象我们手中的股票,债券和外汇所表征的财富一样,随时都可能消失。
量子的这种解释是许多年之后物理学家才认识到的,当时可没人这么想。普朗克引进量子这个词语纯粹是为了解释十九世纪末的两朵乌云之二–黑体辐射中的紫外灾难。
首先来说说什么是黑体,黑体是完全吸收落在它面上电磁波的物质,所以我们称之为黑。我们已经知道自从迈克斯韦提出他那著名的公式之后,电磁波的范围就变得极广了,从常见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光,到广播电台的长波,短波,从夜视仪发出的红外线到能杀死生物体的紫外线,从探索敌踪的雷达波,到神秘的 X 射线都属于这一范畴。
它们的区别仅在于波长的不同。各种电磁波都是携带能量的,那么我们从黑体上开一个小口,象打开炼钢炉的炉门一样,测量辐射的电磁波携带能量和辐射频率,就会得到一条曲线。
如何解释这条曲线是一直困扰所有物理学家的问题。琼斯曾经提出一个公式,在长波阶段符合得很好,但这个公式有显然的漏洞,当电磁波的波长一短,譬如在紫外线段,能量会变得很大。按照琼斯的算法,你刚打开微波炉,紫外线强大的能量会顿时将你击毙在地的。这就是著名的紫外灾难。
后来在短波段维恩也提出了一个公式,但适用范围也仅限于短波。
普朗克是个研究辐射问题的专家,他用插值的方法将曲线长波,短波两头都连接了起来,提出自己的公式,结果非常完美。在推导过程中,他引入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和一个神秘的常数。
他的假设是能量是一份份传递和吸收的,而每一份能量都和一个非常小的常数有关。
这对当时所有的物理学家来说,不异于晴空霹雳。
从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人们的潜意识中认定世界是连续的。所谓连续的意思是物质是可以任意分割的,上帝不喜欢整数。研究数论的数学家可能不喜欢这句话,可是在大部分物理学家看来,如果不研究小数点后的东西,整个自然界就没有意义了。
你可以从一根连续的线上,随便剪下任意的一段长度。你也可以从一杯水中喝掉任意任意少的水。而物理学家们总喜欢把物体或者运动分成无穷小段来考虑,这已经成为惯例。反正拉丁语中有一句经典名言:自然不突变(Natura non facit saltus)。
而普朗克大声地告诉我们,不是这个样子的。不可能存在一点五或二点五个量子之类的说法。能量的最小份额就是一个量子所携带的能量,普朗克给出的公式是 。BD是电磁波的频率,而 h 则按照惯例命名为普朗克常数。这个原本拼凑出来的常数竟成了物理上最著名的三个常数之一,另外的一个是牛顿万有引力常数 G,光在真空中传播的速度 c。黑体辐射的任何能量都是它的整数倍。
纵使普朗克在学界威望了得,大部分人也没有在意他的假说。但是有个年青人却深刻地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他就是爱因斯坦。
造化弄人。爱因斯坦自己也没想到亲自接生的量子力学若干年后竟成他发誓也要扼死的对象,要不是玻尔一帮人的精心呵护,量子力学的命运还不知会怎么样呢。
爱因斯坦的光量子理论是解释光是如何射到金属表面打出电子的。这在物理学上称为光电效应。19 世纪物理学最成功的理论之一是推翻了牛顿的光粒子学说,确立了光的波动学说,而迈克斯韦方程则将光牢牢钉到电磁波中去,无数的实验证明了这一结论。
但是光电效应和看来确凿无疑的波动理论格格不入。简单点说,光更象一个个粒子钻入原子,并将电子硬碰出来,就象小孩子们常玩的弹子一样。而每一个粒子,按爱因斯坦的说法,就是普朗克提出的量子,能量不可再分的那一种。
几乎每个物理学家对这个解说都在大摇其头。关于光是粒子还是波的说法人们已经争了几百年,好不容易将光验明正身收了场。不料,爱因斯坦却将旧案翻了过来。
还是让事实来讲话吧。
检查的方法很明确,你不是赞成光是粒子么。那么所有的粒子都具有动量(质量与速度的乘积),那你找到光存在动量的证据不就完了。
重任落在美国物理学家康普顿身上。
康普顿是个研究射线的专家。他既喜欢拉提琴,也喜欢打网球,而且由于出了名的力气大,不仅经常拉断琴弦,而且打出网球的速度简直比得上他研究的宇宙射线。当然他最喜欢的还是跑便全球测量各地宇宙射线的强度。
一次,他带上设备远赴墨西哥。在站台上,人们看到一个轻松的美国绅士手拄文明棍,后面跟着一大队被仪器压弯了腰的墨西哥小伙,警察检查行李的时候,认定他那宝贝仪器是用来造炸弹用的。可怜的康普顿即使衣冠楚楚,也不得不在龌龊的拘留室中留了一宿。
康普顿将 X 射线入射到石墨晶体上,并在其背面测得散射的 X 射线的波长有位移。这称为康普顿效应。
用康普顿自己在的论文《X 射线在轻元素上散射的量子理论》作出的结语来说:"对这个理论的实验证明,非常令人信服地证明,辐射光子既带有能量,又带有定向的动量。"
看来原有的观念需要再次更新,人们不得不尴尬地接受光既是粒子,也是波的看法。
不要感到不习惯,这里蕴藏着一个更本质的思想,直接促使了量子力学的诞生,可是纵使天才如爱因斯坦当时也没有深想下去。
1911 年的第一界索尔维会议的气氛是沉闷的。
索尔维本人是个比利时的化学工业家,曾因获得氨碱法制碱的专利而发了大财。这位科学致富的知识分子对物理学,尤其是理论物理学情有独钟,虽然自己在这方面无甚造诣,却可以请到世界上第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来到布鲁塞尔召开国际性物理会议。
这次会议聚集了二十三位欧洲一等一的物理学人才。他们面无表情地听完了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报告。即使在距提出普朗克常数 11 年之久,普朗克仍小心翼翼地用上假设的字眼儿。而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在那时也不过被认为是毛头小伙变的魔术而已。
两个宇宙常数,h 和 c 都在那时提出,它们一个代表宏观,一个代表微观,但都没得到一致的确认。光速 c 是相对论中必不可少的基础,而没有普朗克常数,后来的量子力学无从谈起。
最后,会议的发起者,老态龙钟的洛仑兹站起来发言,老人的声音有些含混:
"非常有可能,在我们这些人在这里讨论这些复杂混乱的问题时,在地球上某个僻静的角落,某一个思想家已经解决了它。"
所有在座的人都沉默不语。
没有人料到路该怎么走下去,因为此时,
—26岁的尼尔斯.玻尔还在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卢瑟福手下当助手,每天揉着红红的眼睛苦无收获。
—11岁的维也纳中学生泡利深更半夜一个人跑到野外观察星象。
—10岁的海森堡已经可以流畅地奏出巴赫的狂想曲。
—9岁的狄拉克经常沉默地缩在教室一角。
—3岁的朗道已显现顽强执拗的天性。
尼尔斯.玻尔是一个典型的丹麦人,尤其令人难忘的是他的大鼻子。如果看到他父亲和兄弟的照片,就会明白这是他们家族的标志之一。
小时候玻尔就活泼好动,他经常喜欢顺着螺旋型的爬梯攀到钟塔的最顶一层,每每会引起在塔下的教堂中祈祷的大人们的阵阵惊叫。更奇怪的是小玻尔这么做既不是和伙伴们好勇斗狠,也不是为了眺望远处海港里的片片白帆,而仅仅想了解大钟的指针到底是怎么转动的。
很难想象一个几岁的小孩会对密密麻麻的齿轮感兴趣。但在玻尔家里看来这绝对算不上好事,这是玻尔的父亲一次下班回来发现玻尔坐在地上把家里唯一的大挂钟解构成一堆齿轮和发条时深刻意识到的。
很快小玻尔成为家里的义务修理师,但是经玻尔修理过的东西显然起色不大。
慢慢大家发现,与其说玻尔是想把它修好,还不如说他仅仅是想了解其中的结构而已。
一次,玻尔选中了父亲那辆还算新的脚踏车,不过这可是个大家伙,一个人对付不了。玻尔发动了自己的小伙伴们,孩子们一番努力将车的飞轮卸了下来。到往上在装的时候可就犯了难。这时玻尔发挥了自己的天赋的领导才能,他有条不紊地指挥这个扶住车子,那个紧上螺丝,大家忙了一上午总算装拼成功,虽然第二天玻尔倒霉的父亲刚骑上去不久,飞轮就在主人的惊呼声中远远地飞了出去
这是玻尔第一次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有些事情纵使是天才也不能独自完成的,若干年后玻尔组织一批人象拆卸那辆自行车一般拆卸原子时,心中的想法也是一样的。
在玻尔读书的时候,小伙子在物理和数学上的逼人才气已经展现出来。他的弟弟海拉德,拆卸飞轮时的"帮凶"之一,亦是聪敏过人。在球场上,兄弟俩一个充任中卫,一个担当门将。但是球风凶悍的海拉德的辛苦往往被漫不经心的门将玻尔所废弃。往往当球朝球门直飞来的时候,玻尔的脑子里还在转着些复杂的公式。他命中注定不是来扑救这种黑白相间的足球的,而是一种叫原子的小球的
这时的玻尔在学生中的印象是迟钝,不光踢球时如此,平时任何一件事反应最慢的就是此君。和小时相反,现在的玻尔更喜欢沉迷于哲学思辨中。除了哲学和足球之外,自小就手拙的玻尔更喜欢跑到实验室里去。尽管实验室的老师并不欢迎这个创造了一年内打破玻璃器皿的最高记录的学生
一次,实验室里传来轰地一声巨响,连校长室里的人都给惊动了。秘书朝外看也没看就安慰慌乱的校长道:"不要紧,肯定又是那个叫玻尔的学生给弄的。
看来除了玻尔不足称道的实验技能之外,他的好奇心也委实过强了点儿。
但是此时的玻尔已经立志把物理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了,年仅二十一岁的他出手不俗,在一次科学院悬赏征求有关液体表面张力的论文中获得金质奖章,得到当时最有名气的物理学家瑞利的首肯。
这一年当真喜事连连。他的兄弟海拉德作为丹麦队国家队的中场核心在英国举办的奥运会中大显神威,而玻尔作为替补在卖力地挥动着手中的红白两色国旗。赛后,大鼻子兄弟成为丹麦球迷们议论的核心。多少年后,有人看到报纸上玻尔手捧诺贝尔奖的金质奖章的照片时,心里还在纳闷:这个大鼻子看起来怎么就这么眼熟呢?
不久玻尔的博士论文答辩就开始了,他的题目是《金属电子理论的研究》。他又创了一个记录,只用一个小时就以博士的身份离开了学校。希加德教授第一个发言,也只能从文法修辞方面挑些纰漏,其他人则都是不停的赞誉。
小小的答辩室挤满了人,大家都对这个年青人和他的理论感兴趣。不过更使记者感兴趣的是丹麦国家队的成员一个不少地都在那里,球员们都坦然承认他们听不懂玻尔兄弟的讲演,但这并不妨碍帮他们助威,不管在球场上,还是在答辩室里。
但是这次玻尔象在球场上无所事事的守门员一样显然没有扮演重要角色。他讲完匆匆拎起书包就走了,原指望看到法庭里类似的指控和辩诉的情形的人大失所望。
玻尔的理论太过新颖,以至没人能向他发问。
凭心而论玻尔对自己这篇花了两年时间准备的论文是不满意的,里面用了大量的经典公式推出意义不大的结果,他认识到要解决电子之类微观的东西,原有的观念必须舍弃。若是十年以后的玻尔看到这篇文章,他会飞快地揉作一团丢在废纸篓里的。
不过这几年也算没白过,至少他凭自己的才华结识了后来的玻尔夫人,当时年轻貌美的玛格丽特小姐。
经过一个暑假的休憩,玻尔来到了英国的剑桥。这里是公认的物理学的发祥地,如果一个学物理的没有来过这里,仿佛穆斯林没有到过麦加朝觐。在这座宁静的校园里升起过多少辉煌的明星呵。仅牛顿一人就称得上气盖百世。他的耳畔想起了斯宾塞的诗句:
"剑桥,我的母亲,
在她那顶冠冕上,
缀有多少睿智,多少冥思......"

当他漫步在三一学院时,总感到巨人牛顿的眼光在不远处盯着自己。牛顿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这里的每寸土地都留有他的脚印,他曾经坐在这里的草坪上和热心的学子们讨论上帝之谜,也许就是在这棵苹果树下悟出了万有引力定律。最终是他使三一学院的威名远播,而学院院长的职位成了学界荣耀的象征。
玻尔工作的单位就在卡文迪许实验室,人们怎么也没想到他竟和主任卢瑟福先生成了莫逆之交。他们一个身高体壮,声若洪钟,一个温文尔雅,慢声细气一个来自新西兰的农庄,一个出身于哥本哈根大学的教授家庭一个脾气暴躁,一个内向迟钝。再想找两个脾性反差如此之大的人只怕就不易,他们怎能谈的来呢?而且玻尔的实验能力实在不敢恭维,可卢瑟福总是一副信任有加的样子。
卢瑟福的想法是卡文迪许实验室能动手的人着实不少,但是真正具有物理头脑,并兼备深厚的数学功底的人并不为多。玻尔这个人看似迟钝,但他的思想磅礴大气,浑然天成,别人是万万比不来的。而卢瑟福本人的理论功底算不上突出,这就更需要人在旁边辅佐。
卢瑟福的成功的实验引起玻尔很大的兴趣,他整天纠缠于线圈和导线之间。闲暇的时候则是在思考卢瑟福的原子结构。显然,这个模型也有经典物理所不能理解的内容,电子在核内如此高速地运转,为何能量不会耗尽呢?这个问题是致命的。此时的玻尔有幸了解到普朗克的量子假说,或许卢瑟福原子中的电子也是受量子作用支配的呢?
他开始通过计算来验证自己的想法,往往从早忙到晚。连素来精力过人的卢瑟福也不由得叹服。但结果却总是不如人意,捣蛋的原子是不肯轻易就范的。一切都是苦无头绪。
从此玻尔象换了个人一般。晚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白色的幽灵在实验室徘徊,深夜里还听的见单调的皮鞋声。白天则一动不动的坐着,脸上仿佛失去了表情,眼睛也是浑浊的,简直是个痴呆症患者,连卢瑟福也暗暗担心了。
终于有一天,玻尔突然径直站了起来,冷静地说道:"也许我知道了什么。"然后麻木已久的脸上微微泛出红润。
"你们谁能告诉我关于原子和电子的性质,越详细越好。"当玻尔准备走出大门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什么回过了头。
一个同事向他介绍道,原子的化学性质呀,磁性呀,旋转呀,光谱公式呀......
"等等,光谱哪有什么公式?"玻尔突然打断道。
"你会不知道光谱公式?"同事迷惑地望着他,但还是不厌其烦地讲起来这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公式,如何解决了很多问题。
玻尔没等他说完,就飞奔图书馆。马上他就查到了那篇短短的巴尔末公式。这个公式因为形式完美,几乎所有的理论物理学家都知道,偏偏玻尔将它漏过。
玻尔那双锋利的眼睛仅仅扫过几行,他就听见自己心脏的强烈跳动了,找的就是它!
那时侯人们研究原子最有效的方法是观察它的光谱。牛顿当年就让一束日光通过三棱镜,分成七种颜色,这实际上就是光谱。后来在 19 世纪,英国的沃莱斯顿和德国的夫琅和费分别发现了太阳光中总有几条暗线,后来发现暗线达上千条之多。
随着实验的发展,人们发现在酒精灯的火焰上撒上食盐(氯化钠),就会观察到一条宽阔的黄色光谱。这实际上就是钠元素本身的标志。每种元素都有自己的标志。只要该种元素存在,哪怕只有极少一点儿,也会观察出来。而太阳光中的暗线则意味着阳光在穿越这些元素时遭到吸收。于是我们只须对照一下光谱本上的光谱,就会查到太阳上有什么元素。有些神秘的暗线则意味着新元素的出现。然而原子发光的秘密始终没人给出合理的解释,现在轮到玻尔了。
中学教员巴尔末是在 1885 年提出这个公式的,那次也属偶然。他闲来无事,将氢原子的几条谱线的波长的数值当一般的数字游戏玩耍,它们是 6526.79,4861.33,4340.45,4101.73 等等。但是很快发现了一个惊人的规律,每一个数字都是和一个自然数相关的,比如 6526.79 正比于3 ,4861.33 正比于4 ,4340.45 正比于5等等。
这是个了不起的发现,可是谁也将它解释不了,在一次学界聚会的最后一天晚上,两个物理学家为明天的远别在一家酒店干完最后一杯。小个的中年人紧紧拥抱着大个的年青人,并送他一个笔记本作为纪念。大个的那个则终生也忘不了扉页题的词:"什么时候解决了巴尔末的公式之迷,我一定请你在这个酒店痛饮葡萄酒。"小个的教授名字叫索末菲,大个的年青人叫德拜。,他们都是后来对量子力学的发展作出贡献的人。
玻尔可不这样认为,在向来充斥着小数点的物理学里居然会出现 1,2,3 之类的整数,这和普朗克的量子观点不谋而合。看来古希腊毕达哥拉斯鼓吹上帝偏爱自然数也是有其道理的。光谱公式两个最普通的地方,泄露了上帝的秘密。减号和数字 3,4,5,6 的交替。玻尔经过深思熟虑后,终于发现了真理。
减号的两端联系了两个和整数相关的量。因为第一个数减去第二个数,就产生了一分频率固定的光。而巴尔末公式里的平方的倒数使玻尔更是激动不已:电子绕原子核旋转时的能量也是和平方成反比的呀。这样说来,减号两端的量都是和原子能量相关的。事情到此再清楚不过了,光所带走的能量就是原子所失去的能量。原子发光看似神秘,说穿了却也很平常。
显然原子的能量不是连续的,而象阶梯一样是一步步的。每个阶梯对应的能量叫做能级。每一个能级对于电子这辆微型汽车来说都是一条公路,可是调皮的电子可以从一条公路跳到另一条公路,而不怕交警递给它的罚单。当电子从高能级跳到低能级的时候,就会发出光线当光线从原子经过的时候,就会将其中的几根光线吸收。无论发射还是吸收,导致原子能量的变化与神秘的普朗克常数有关。从而氢原子的各条光谱是由原子跃迁的始末能级,当然与整数有关了。
而且,玻尔断言在每一个能级上原子是绝对稳定的,不会朝外辐射能量。即使辐射能量,原子也是一次就发出的,发射完原子又恢复到稳定的状态。这样卢瑟福关于原子结构的行星模型的稳定性也得到了解释,真是一举几得。
玻尔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整理出来,交给卢瑟福看。不久他就收到答复:你的理论在解释氢原子光谱上算得上是完美卓绝,可是你又怎能把普朗克的奇怪理论和经典力学结合在一起呢?
实验物理学家接受新思想总是比作理论的人慢上一拍。卢瑟福也不例外,作为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他还不能理解普朗克那些无用的量子究竟会在自己的实验室里扮演什么角色。
在他看来,一个电子就象是绕着花朵飞舞的蜜蜂一般。他提出反驳玻尔的论据是:请你说出电子从一个稳定状态跳到另一个稳定状态,它是怎样决定自己的频率呢?难道电子事先就知道自己该落在哪条轨道上?
玻尔当时就是一愣,迟钝的他不可能当场找到辩词的。不过玻尔是个痴迷的人,立时没想通的事情过后也要慢慢想。这时他的脑海里第一次升起"概率"这个词,电子从高能级跃迁下来,它到任何一条轨道都是有一定几率的,就象赌徒们扔下骰子,他也把准自己会扔到 1 还是扔到 6。这个观念最终导致了量子力学的几率解释,从而引发了一场亘古未有的大辩论。当时玻尔还想不到这么深远,但他觉得一个新理论出来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要有一点合理的地方就应该来出来让大家讨论,何况它还很完美地解释了氢原子发光的问题呢。
玻尔斟词酌句地在论文中展出了自己的思想,经过反复修改,终于完稿。卢瑟福看了之后,笑道,你这篇论文未免也太长了,英国人可是跟你们可是不同呢,他们总是以简洁为美,而你们日尔曼更喜欢长篇大论。
可是在玻尔看来,从这篇每个单词都是心血的论文中删掉一些东西,还不如挖掉自己的肉呢。不过,玻尔也有办法,他将自己题为《论原子和分子结构》的论文分成三部分发表在《哲学杂志》上。于是,玻尔著名的"三步曲"诞生了。
在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中,玻尔将普朗克的量子理论引入到卢瑟福的原子模型中去,并且提出能量的发射和吸收并不象以前人们认为的那样是连续的,而仅仅是原子从一种稳定状态过度到另一种稳定状态时才具有的。原子处于通常的状态时,无论电子怎么转都是稳定的。
学界从玻尔造成的轩然大波中清醒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让玻尔提供实验证据。这对玻尔来说是傻眼了,但绝难不倒卢瑟福。他给他的老友伊万斯去信让他去测量氦气的光谱。
玻尔的论文中预言了皮克林和福勒发现的几条光谱线不是属于氢,而是属于氦的。当伊万斯这位实验老手将纯净的氦气充满玻璃试管并测量后,验证了玻尔的结论。
福勒本人不同意玻尔的结论,他这些即使是氦的光谱它们的波长也和玻尔计算的有偏差。玻尔则认定福勒所测到的只不过是被剥夺了一个电子的氦原子的光谱经过修
正玻尔把他这种偏离了的光谱也计算出来,和福勒的数据完全吻合。自此玻尔的大名和他的理论远播欧陆。
当在维也纳的爱因斯坦知道这个消息时,也是大吃一惊。他当即认为这是人类少有的重大发现之一,但是在一次聚会上,爱因斯坦终于支支吾吾地说了句坦白话:"我想,可能在某一天,我也产生过类似的想法,可我没有勇气公布于众......"
千万不要用世俗的眼光去看爱因斯坦,认为他的这个马后炮不过是在挽回自己的面子。爱因斯坦一贯是个严肃而认真的人,何况他当时正在从事高难度的引力理论,这一点也不损害他的形象。
如果把物理学家比作与上帝弈棋的人,爱因斯坦则是思路深远的高手,他深知这一步下去会导致怎样的结果。这最终将会使得概率观点在人们对自然界的解释中与站上
风,但这与他终身信仰的决定论思想是尖锐矛盾的。
若干年后,他孤身一人面对众多信奉量子力学的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我不相信上帝会掷骰子。"
爱因斯坦和学界的分歧就起源于此时,但当时爱因斯坦是想不到那么多的。他以无比的兴奋赞扬道:
"这些不牢靠而且互相矛盾着的基本原则,却足以能使具有玻尔那样独特直觉和理解力的人发现光谱线和原子电子壳层的一些重要定理,无论怎么看来都是一场奇迹。仅此一项,玻尔便可名垂千史。"
(未完待续,关注社区期待后续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