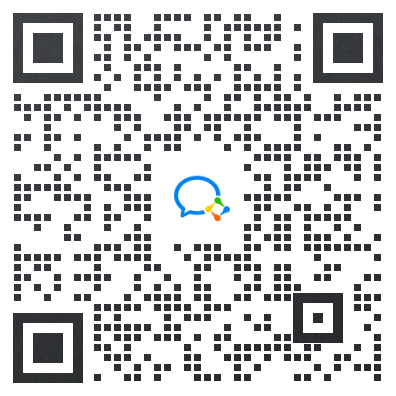写在前面
大约13年前,北大的BBS上一群热血青年对于“量子力学”展开了激烈讨论,有那么几位物理学爱好者分别认领了自己的科学偶像,以人物传记的形式,用不同的角度记录了量子力学的发展。
小编恰好认识作者中的一位,这篇是以“玻尔”为人物主线进行记录的,感谢原作者“时间的孩子”的分享,也希望借助此文的传播能使得当年那群热血青年重聚。

玻尔象个在田间劳作了一年的老农,现在他要收获他的果实了,他首先把目光集中到了元素周期表。

元素周期表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由俄国的门捷列夫提出来的。当时无论在什么人看来这都是人类的一次巨大胜利。门捷列夫根据周期表预言了几种新元素,类铝(镓),类硼(钪),类硅(锗)最后一一得到证实,从而元素周期表的名字传便全球。
玻尔根据自己的三步曲提出原子核外有电子在绕它转动,最简单的氢原子外层只有一个电子,然后随着原子序数而逐渐增加,并形成周期律。当时最多的是核外面有92 个电子。它们在玻尔计算的轨道上一层层垒起来,象儿童们搭的积木一样。既然从没有人象玻尔那样对元素周期律的本质了解地如此深入,那么玻尔也该对元素周期律说些什么了。
这时卡文迪许实验室里精干的小伙子莫塞莱帮了玻尔的忙。他原来一直再和理查·达尔文(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的孙子)联手在曼彻斯特研究 X 射线,当他一了解玻尔的理论,就找到玻尔要求合作。
当时,大部分人认为玻尔的理论不过是一堆数学游戏而已,而莫塞莱决心在 X射线上为玻尔找到证据。他的想法是:X 射线是从原子内部的电子产生的,那么我只要测得一系列元素的 X 射线谱,那么不就可以验证玻尔的结论了?
在实验室里人们向来公认莫塞莱的活力是不下主任卢瑟福的。从下午 3 点到晚上 3 点,他都泡在了实验室。很快他找到了需要的东西,一个长一码,直径一英尺的玻璃圆桶,在圆桶中心放上了一节玩具火车和轨道,在 X 射线的照射下,将盛着样品小车拉来拉去。
底片的结果是惊人的,它们呈现出周期性的变化,玻尔胜利了。
在论文中莫塞莱指出他的这种方法还可用来发现一些"失踪"的元素,并预言这些元素光谱的性质。以电量为一个单位,在一号元素氢和九十二号元素铀之间,只有第四十二,第四十三,第七十二和第七十五号元素没有发现。没有几年莫塞莱预言的元素均被找到。
自此莫塞莱成功地解释了周期律,这是当时与卢瑟福发现原子核,玻尔解释氢原子发光并称的物理学三大发现。而这三大发现本身又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开始笼罩了欧洲。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小伙子们都走了,波林去了兵工厂,弗劳伦斯和安德拉德当了炮兵,就连闻名学界的莫塞莱也穿上了威武的军装。
不过莫塞莱是真心实意地为国家背上步枪的。他本来作为杰出的学者,有权拒绝兵役的。但他作为英格兰人,国家开仗而自己龟缩在后方实在是耻辱。他脱下白大褂,戴上钢盔,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离开了实验室。在离开之前,他把心爱的仪器—X 光机擦了又擦,并一再叮嘱手拙的玻尔千万不要弄坏了。
卢瑟福有力地握住了莫塞莱的手,并用他那特有的坚定的眼神向他预祝好运。而一向沉默的玻尔也絮絮叨叨地要他注意安全。
莫塞莱是天生的乐天派,他耸了耸身上的肌肉让忧心忡忡的人们放心。当他走出院子时,还传来他那高亢的声音:"再见了,朋友们,我还要回来的!"
卢瑟福和玻尔以为他们的实验室办不下去了,适龄的年青人都在战场上,而无论是官方还是私人对实验室投资的兴趣都不大了。最重要的是赢得战争,哪还顾得上原子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第二天玻尔心情惆怅地走到报告厅门口,往常这里应该挤满了人来听这位原子大师的讲座。
今天也许只有我一个人了吧,玻尔边想边走了进去。
大出玻尔意外的是,大厅里仍然坐满了人!所有人的目光中充满了激情。
看来即使在最战乱的时候,也不能阻止人们对科学的向往。
玻尔和卢瑟福分外忙碌,很多人走了,剩下的活只能自己干。战争年月讯息也被中断了,他们不知道同盟国那边的同行们的研究进展到何种地步,更不知道实验室里那群生龙活虎的小伙子们现在是死是活。他们在一起除了讨论物理问题,就是诅咒什么时候这该死的战争究竟会结束。
一天下午,玻尔顺手接过了看门人递给他的报纸,上面的头版是"海军大臣丘吉尔的疏忽导致加里波第半岛的冒险惨遭失败。"他也没有认真读,就塞在纸篓里。当时报上的此类消息实在太多了。
但是紧接而来的消息让玻尔和卢瑟福都大吃一惊,他们知心的同事,几个月前还活蹦乱挑的棒小伙,学界难得的人才莫塞莱在那场战役中牺牲了。
莫塞莱死了!!
玻尔难过地弯下腰来直捶自己的脑袋,后悔当初该劝住他不要上战场的。而素来洒脱过人的卢瑟福的眼睛也闪出了晶莹的泪花。
玻尔怎么也难想象那颗无知的子弹是怎样击中了莫塞莱的心脏,而莫塞莱又是怎样倒在泥泞的战壕里痛苦地挣扎。当人类仅因击毙一个士兵而多了一枚爱国勋章时,金灿灿的诺贝尔物理奖奖章却注定不能落在这位极有才气的年青人身上,那年他才仅仅二十七岁。

(左起玻尔,奥本海默,费曼,以及费米)
天昏地暗的一次大战总算结束了,战场上幸存的小伙子们纷纷回到实验室,然而玻尔要离开实验室和陪他度过生命中的黄金岁月并一起经历过战争煎熬的同事们了。他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另外开创一番事业。
卢瑟福一直送他到码头,一路上向来健谈的他沉默不语,倒是玻尔不停地找到话题。
海阔天蓝,远处的游弋的渔船还没来得及拆下炮架,朝阳下的彩霞似乎仍被硝烟所弥染。
玻尔登上船头时仍不停地向卢瑟福挥着手,他和卢瑟福心里都明白,如果玻尔不走,卢瑟福退休后一定会把当时这座世界上最好的实验室的主任让给他的,这是让任何物理学家梦寐以求的职位,然而玻尔深知自己在实验上并无天赋,他决心回到哥本哈根去建立一个专门从事理论工作的研究所。
1920 年 9 月 15 日,正是丹麦云雾弥漫的秋季,哥本哈根大学的理论物理研究所正式挂上了招牌。选在这样的日子里,可能预示着这个研究所的一群年青人最终会为人类在迷雾中探出一条路来的。
玻尔是以怎样高兴的心情迎接来宾的呀,开幕式上坐满了物理学界的精英。玻尔用他那低沉的嗓音打动着听众:
"我们知道,在科学的发展史上,一个人通常是不能确保自己是有所建树的。很可能出现一些障碍,只有新的观点才能克服它们。因此,特别重要的是不能只依靠个别科学家的天才。
在这里我们将持续产生具备科学方法并能出成果的年青科学家,这一任务要通过我们激烈的讨论来进行。在年青人作出贡献的同时,新的血液和新的观点也会问世。"
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来。
更令玻尔激动的是见到了久别的良师益友卢瑟福教授。这位教授和玻尔一家刚见面就把玻尔四岁的大儿子克里斯蒂安一把抱起来,
吓得小家伙伏在那个新西兰人宽阔的肩膀上哭了。
玻尔热情地带着客人们参观这座新建筑。走上几步台阶,穿过一扇双层大门,就来到了前厅和报告厅。报告厅里排满了阶梯式座位,前排是一面大得惊人的黑板,很多重要的公式将在这里讨论。
图书馆在二楼,从窗户里可以看见公园里恬静的老人坐在长椅上,而孩子们在草地上尽情嬉戏
最上一层是餐厅,咖啡,奶酪和丹麦三明治是常年供应的。后来证明,在这里喝咖啡聊天所诞生的新思想比正式的讨论班上还要多。
其余的房间是实验室和办公室,但是既然挂的是理论研究的招牌,所谓实验室就形同虚设了,它经常成了闲暇时工作人员打乒乓球的去处。
当 1921 年 1 月 18 日,研究所正式开张后,玻尔把自己的书籍和文稿都搬进办公室来了。他坐在办公桌前,掏出钢笔吸饱了墨水,在信纸上写下第一封信–当然是给卢瑟福。这个研究所很快就要成为自古希腊的柏拉图学院以来最负盛名得研究中心了。
1922 年 11 月里的一天下午,伏在办公桌上奋笔急书的玻尔突然接到了从瑞典斯德哥尔摩来的电话。电话里委婉地说道,玻尔教授最近是否有空到斯德哥尔摩来一趟?
玻尔睁大了眼睛,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奖的桂冠将落到自己头上,怎么不令人兴奋呢?他马上回家把这个喜讯告诉自己的妻子。
结果一贯迟钝的玻尔又慢了一拍,几乎哥本哈根全城的人都比他知道得早,走在路上即使连街头卖冰淇淋的老头都向他打招呼表示祝贺,而他美丽的妻子不仅早就精心准备了佳肴,而且特地把家里珍藏的香槟酒拿了出来,一进门孩子们纷纷献上带巧克力味的吻。玻尔和家人们欢聚了一夜。
全丹麦的人都被惊动了,人们没有想到这个向来只出产小麦和牛肉的小国会出现一个大科学家。玻尔一回到实验室就被同事们抛的彩带罩了一满头,有人捧来了蛋糕,有人奏起了小夜曲。
世界各地的电报象雪片一般飞来,但是玻尔最先接到的自然是来自英国卡文迪许实验室里的那一封。卢瑟福在电报中祝贺道: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衷心祝贺你荣膺诺贝尔奖,而且大家都知道,这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这是对你杰出工作的最高确认,最后祝你在斯德哥尔摩愉快。"
文如其人,卢瑟福还是那样快言快语。玻尔手捧着电报深深地激动了,他回想起在实验室里 12 年来的日日夜夜,那些亲如兄弟的战友们,还有这位亦师亦友的新西兰大汉。
12 月 10 日是诺贝尔的诞辰,也是诺贝尔奖颁发的时候。斯德哥尔摩的大街上积雪很深,斜斜的阳光下,印有黄十字的瑞典国旗在微风中飘荡,这说明今天是多么重要的一天。
玻尔和当年的化学奖得主阿斯顿,文学奖得主西班牙作家贝拿凡塔一起坐在了领奖台上。
"尼尔斯.玻尔!"当这个名字回荡在大厅中时,玻尔站起来向观众鞠躬致意。大会主席郑重地宣布:"鉴于他在原子结构和原子放射性的研究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而授予他诺贝尔奖金。"
然后按照大会的例程,玻尔要发表演讲
他简要回顾了人类在最近二十年对原子结构的研究成果和自己提出的新猜想。
然后他宣布了一条激动人心的消息:元素周期表上第七十二号元素已经找到了,按照玻尔的理论这个失踪了的元素应该和第二十二号元素钛,第四十号元素锆的性质应该相近,而不是和它临近的稀土族的元素性质相似。
这是研究所里的好友海乌希送给玻尔最好的礼物。他和另一个名叫考斯特的荷兰人合作,用 X 射线分析了各种矿石,终于把这个神秘的元素找了出来。海乌希在玻尔受奖的前一天晚上打电话告诉他这一喜讯,电话那端的玻尔沉默了一会,问这种新元素给起了什么名字,海乌希说就叫铪吧,这是取自哥本哈根的旧名哈弗尼亚的头一个音节。
讲到这里,玻尔的声音有些哽咽,他想起了莫塞莱,那个最早预言铪的小伙子,要是他今天在这里会是多么兴奋呀!
最后玻尔象预言家一般加上了告诫性的话,目前我们的理论还刚刚开始,还远谈不上完备,前进的道路还是曲折的,也许我们的思想还要进行进一步的更新。
玻尔回到哥本哈根不久,就碰到了件尴尬事。当研究所的同事们还在高声欢呼铪的诞生时,一位头发花白的爱尔兰老化学家就提着试管找到了玻尔,他声称早在 1913年就找到了这个神秘的七十二号元素,并且他早就为它取好了名字,叫做"锯",以纪念爱尔兰的古老部落倨尔特人。
研究所里的人有的吃惊,有的愤怒,这不把玻尔多年的心血否认了吗?而玻尔本人在屋里转来转去。玻尔是个老实人,不知道怎么说服这个倔强的老头儿而又不伤他的自尊心。不过最终玻尔还是鼓起勇气告诉他:他的样品是经不起 X 光机下的检验的。可怜的老头儿还处在上个世纪用酒精灯和试管来研究物质的时代,他可从没见过如此设备庞杂的 X 光机,他徒劳地争辩了几句,最终还是悻悻地走了。
这只不过是研究所的小插曲而已,事实上当时很多物理学家,不管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都不是对玻尔的半经典半量子的理论很满意的。
卢瑟福就曾经这样跟玻尔笑着说,我说尼尔斯,你干脆向物理学家们建议每星期一、三、五都采用经典的规律,每逢二、四、六就采用新的量子学得了。
在 1913 年英国的一次物理学例会上,人们纷纷请德高望重的经典物理学家莱列勋爵发表一下对当前物理学的看法。
老莱列首先说,自己作为一个超过 60 岁的老人,就不应该对物理学的新思想指手划脚,大家都被老人的坦诚所感动。但是很快莱列就加上了这样的话:"但我还是很难相信,玻尔他们的想法就能反映自然界正确的一面。"
不光是年纪大的人,德国年轻有为的实验物理学家奥托?斯特恩比玻尔还小三岁,就曾当众说道:"要是他们(指玻尔)的胡说八道都是真的,那我只好转行了!"
威望向来孚众的英国皇家学会会长汤姆逊根本不相信玻尔的理论,他认为玻尔任意规定的量子化条件只不过在掩盖无知。
革命的一派则怎么也找不到更新的想法。
解铃还需系玲人,玻尔自己引出的麻烦还得自己来解决,1922 的玻尔虽然身获诺贝尔奖已算功成名就,但他当时发展的那套叫做旧量子论,这离量子力学的真正建立还
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打破这个僵局先是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人。
德布罗意踏入物理这行不过几年,但是他身份特殊,他是法兰西波旁王朝的王族中人九百年来唯一走入物理学领域的人,虽然他这一支家族曾为法兰西贡献了一个总理,两个议长,两个上将。德布罗意当时的称谓是亲王。这位亲王决心用实际行动证明,这个皇室的后人也会象泥瓦匠的后裔高斯,农场主的儿子卢瑟福一样成为科学上的巨人的。
事实证明他不仅是皇室中的王子,而且在当时的物理学界也确实扮演了王子的角色。
在轰轰烈烈的一战中,德布罗意也走上了战场。不过他的职位还算安全,不过是个测绘员。但是战场上枯寂的日子也是很难打发的,他可不愿和无聊的士兵们整天甩纸牌。
他虽然取得过文学硕士学位,但在这段时间对物理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风行一时的量子理论钻研甚深。不过他总隐隐觉到这套理论有缺憾,具体在什么地方一时也难明了。
一天晚上,他坐在土岗上一边思考一边望着夜空,突然一颗流星划过了天际,他的灵感马上被激发出来:
我们费了那么多劲来证实了光既是粒子也是一种波,干吗不把这进一步推广出去呢?比如说新发现的电子,我们以前总是把它当成点粒子,难道不能用波动观点去看待它?事实上,不光是电子,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具有和光一样的性质:波粒二象性。
我们眼中的所有事物都是在象水波一样地振动着的,还有比这更奇怪的么?
战争结束后的 1924 年,德布罗意把他的想法整理在博士论文《量子理论的研究》中。
古老的索尔蓬纳大学的答辩会上,人们交头接耳,都在议论这个这个文学硕士如何应对评委们尖锐的反诘的。
德布罗意在黑板上写下他那著名的公式:
![]()
这是用来说明电子的波长的,p 就是物体的动量(质量和速度的乘积),h 则是微观世界的钥匙–普朗克常数,λ 则是波长。如此简明的公式蕴涵的意义是深远的,所以尽管他的论文没有得到实验的支持,而且还引起评审委员会的人一阵骚动,但是还是主持答辩的著名物理学家郎之万鼎力坚持下通过。
郎之万的评语是:
"这个博士生的想法近似荒诞,但是其中物理思想展现的很是完美动人。"
这个和爱因斯坦一样深信自然的和谐与美的教授心里尽管一百个赞成德布罗意的见解,但嘴上还是要跟评委们敷衍过去的。
当几天后他把这个博士生的思想转述给好友爱因斯坦听时,巨人罕见地沉默了好久,他送别郎之万时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至此,一场伟大戏剧的帷幕被人掀开了一角。"
无论如何,德布罗意的这篇论文是人类历史上物理学上最出色的博士论文,1929 年他凭此获得诺贝尔奖,这也开创了博士论文得诺贝尔奖的先例。
很快德布罗意的思想得到爱因斯坦的欣赏的消息传了出去,人们还是崇拜伟人的,所以都认真地将他的文章读了几遍。这篇论文观点倒是很有轰动性,很多人都觉得自己都曾产生过类似的想法,只不过从来没有人象德布罗意那样如此清晰地表明而已。
可是物理学究竟是一门实验的科学,不能仅沉溺在思想的深刻和数学的美妙上。
德布罗意提出了验证的办法,这跟当年康普顿证明光是粒子反过来,我们证明一下电子也有波动的性质就完了。最简单的是波动有衍射现象,即当电子准直地通过小孔时,并不是简单地在屏后打出一个亮点,而是和光一样出现环行的衍射光斑。
正如几年前如果搞 X 光最拿手的是莫塞莱的话,那么现在公认的搞电子的实验大师是亚历山大·多维叶。德布罗意毫不犹豫地找到了他,向他讲述了自己的计划。不料多维叶撇撇嘴,对此不屑一顾,他当时正在忙着显象管上的电子扫描的工作。在他看来,德布罗意简直痴人说梦。
结果虽然多维叶在电视的诞生上作出了贡献,但他显然失去了一次得到诺贝尔奖的机会。而另一个倒霉的先生戴维逊早在几年前他在把电子入射到镍晶片时,就发现那些奇怪的光斑,不过他是怎么也不能解释的。还是爱因斯坦说的好:"只有理论才能决定我们可以观察到什么。"这句话听起来似乎荒唐,但它处处得到了证实。
上帝把这个荣誉交给了电子的发现者汤姆逊的儿子,G.P.汤姆逊。这个小汤姆逊成功地观察到电子衍射的图案,并于 1937 年获得诺贝尔奖。
实验证实还是几年以后的事,但先在理论学界引起的风波称得上是波澜壮阔。 首先是在瑞士的苏黎世, 在一次物理学的常规会议上,大家轮流作着报告,最后会议主持人是德拜,就是当年那个曾经发誓也要解决巴尔末公式之谜的人。如果和索末菲分手后他们再约定每当物理学有重大突破时就在那家餐厅里痛饮葡萄酒的话,那么他和索末菲要么就要沦为十足的酒鬼,要么两个人都要破产。因为这些年物理学的进展实在是只能用天翻地覆来形容的。
他把目光盯在了最后一排的教授薛定谔身上,"教授,听说德布罗意的物质波的思想被广泛讨论,您是否能简单作个报告?"
薛定谔站起来就侃侃而谈,他一直对这些方面很是关注。
然后德拜就提出自己的意见,"教授您谈了这么多波动观点,可是您怎么不提出来一个波动方程呢,这在经典物理里是屡见不鲜的呀。"
两个礼拜后,薛定谔再次站到讲台上,他二话没说先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公式:
然后转过身来平静地说道:"先生们,我找到了一个方程。"
这个方程在量子力学中的地位不亚于经典力学中的牛顿定律,它就是著名的薛定谔方程。
量子力学的正式诞生的第一天的面目就显得甚是诡异,人们尚不能明了它的规律,就提出了它的方程。仿佛没有见到人本身,就知道了他的长相。这也说明量子力学的建立并不需要深厚的数学功底,但对没有第一流物理思想的人来说是不可企及的。
薛定谔发展这个方程看似偶然,却也是煞费苦心。刚开始他总想把时髦的相对论引入到方程中去,但是算得的结果总是面目全非。后来他干脆先放弃相对论,开门见山地将经典物理的方程直接转换过来。他原本就是研究波动的大行家,什么纵波,横波,光波,电磁波统通不在话下,很快他就模仿着写出了自己的方程。
这个方程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多人通过计算解释了以前不能解释的量子现象,甚至包括原子的发光问题。大家在数学上是不存在问题的,经典力学积攒了大量完美的公式可用。
不过所有人都困惑的是,方程中的 ψ 究竟是什么东西。连薛定谔自己也搞不明白,注意,这不是一时不明白,而是一世不明白,至少他的理解始终没有得到物理学界主流的认同。
有人写过一首四行诗打趣道:"
薛定谔的普赛(指 ψ),
用处大的不得了,
只有一事尚不明,
普赛究竟为何物。"
更令人吃惊的是一个年青的日尔曼人在此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量子力学。上帝是个蹩足的导演,他要么就不让量子力学出台,要么就一出来就是两个。
这时冒出来的明星,是后来被称为"量子力学总司令"的海森堡。当海森堡十九岁那年第一次听玻尔的学术报告就尖锐地指出几处错误时,玻尔就注意到了他。
海森堡出身德国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他的父亲是慕尼黑大学的古代语言和拜占庭历史学的教授。
他自小聪颖过人,老师给他的评语是:"他既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又不放过问题的细节。"上中学时由于他认为一些基础课程过分简单,而转学高等数学和物理。甚至 16岁的他还帮助一个要考博士的化学系女生复习高等数学,完后用他自己的话说,不知道她懂了没有,反正自己是彻底掌握了高等数学。
他最喜欢是数学,尤其是数论。中学时就尝试证明过费马大定理和哥赫巴德猜想。这两者都是流传百年的数学难题,后者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因为陈景润的神话在民间被简单演绎成了证明一加一如何等于二。
他的钢琴演奏地非常出色,和爱因斯坦的小提琴被认为是物理学界的一时瑜亮。
1920 年,他考入慕尼黑大学,本来他是渴望求师著名的数学教授林德曼的。但是当教授不经意问起海森堡最近在看什么书时,海森堡回答是在看一本名叫《时间,空间,物质》的书。这位教授显然是这类玄奥的哲学是深恶痛绝的,当即警告他说:"如果看这 样的书,那你在数学方面注定是没有前途的!"海森堡悻悻地退了出来,至此他决定全心投向理论物理。
这时他遇上了量子论的一个领袖人物,那个多年前和德拜打赌的那个索末菲。
他是玻尔理论的大力支持者之一,玻尔的原子轨道和能级的理论经他深化后,成为更基本的索末菲量子化条件。这个工作如此干脆漂亮,连玻尔本人亦是击节赞叹。
索末菲的眼光很是了得,他一下子就从几界学生中找出海森堡和另一个叫泡利的新生参加他的理论物理讨论班。
这个泡利是后来量子力学中必不可少的人物。他被学界公认是"上帝之鞭",因为他对物理中的各种理论几乎有种天赋的准确判断的能力。任何人把新理论拿到泡利面前都是簌簌发抖的,他只瞄几眼就能找到致命的错误,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辛劳几分钟内就可能化为乌有。而且你的争辩几乎是无效的,很多学界名流都会宁愿相信泡利这种屡验不爽的"超能力",而不愿相信几十个高手的联名担保或者复杂然而精细的公式推导。
这两个人立刻形影不离,并将这种友谊持续了终生。他们看起来是多么的不同呀:身材纤细的海森堡总是潇洒地穿着风衣,而肥胖的泡利总是晃动着他的硕大的脑袋。
海森堡更喜欢足蹬球鞋到处旅行,泡利则爱好在昏暗的剧院里品着咖啡看歌剧。但是他们在探讨学术问题时都是分外的认真,不过经常是海森堡费劲心机提出的理论被泡利谈笑间否决了。
一次,他们两个人一起上测量弦振动频率的实验课。可是他们一边合作着实验,嘴里还在不停地争论理论问题。泡利原指望象往常一般几句尖锐的话语就将海森堡压得哑口无言,但这次海森堡不肯服输,他们干脆停下实验好好辩论,结果到快下课时才发现实验没有完成。
海森堡使个眼色,在两端固定紧的弦上轻轻弹了一下,泡利马上凑过耳朵听了一下就写下数据,而他们的"数据"居然蒙混过了关。其实,老师也在纳闷,平时这对笨手笨脚的活宝这次的结果怎么会和标准答案一样呢?
和大多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一样,他们两个的实验水平都很逊色。最古怪的还是泡利,他的毛病是所有的仪器在他手里一碰就坏,越是先进的越是如此,这几乎和他永远正确的批判本领一样百验百中。
(未完待续)